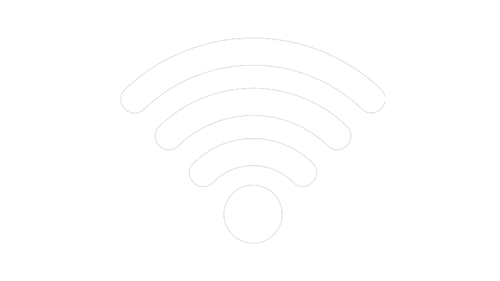从迷茫到觉醒:我的“文革”心路历程
摘要:我是在郴州地区财贸干校工作时,遇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文革”发动群众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声势浩大,轰轰烈烈,前所未有。当时有句话在社会上流传:“老革命...

我是在郴州地区财贸干校工作时,遇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文革”发动群众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声势浩大,轰轰烈烈,前所未有。当时有句话在社会上流传:“老革命遇到了新挑战。”
坦白地讲,我这个“新革命”,当时对“文革”是感到很困惑的:一方面,我非常崇敬毛主席的伟大、英明、正确。我深深懂得,是他在长期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挽救了我们的党,挽救了革命事业。完全可以这样说:“没有毛主席,也就不会有共产党存在,不会有革命胜利,不会有新中国诞生。”我相信,他亲自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也一定是正确的。另一方面呢,我又看到那些“造反派”把所有大大小小的领导,都当成“走资派”来整,要他们头戴高帽、颈挂牌子游街,甚至还高喊“要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还有人真的不讲政策,搞“武斗”,搞“打、砸、抢、抄(家)”。这,我就感到不理解了,从而产生了疑问:这真的是毛主席发动这场运动的本意吗?还是“造反派”在运动中歪曲了毛主席原意,出了差错呢?抑或是有坏人趁机搞“形左实右”,有意破坏这场运动呢?水平低的我,搞不清楚这个问题,头脑迷糊,感到很是困惑。
我这个基层干部,视野不开阔,只看到身边的领导多数思想作风是不错的。比如我的顶头上司王校长,那是一个很优秀的干部呀,怎么也要当成“走资派”来整呢?我回想起了第一次到干校与他共事的一段经历:
1958年,地委作出决策,成立了地区财贸干校,并将王宗柏同志调任副校长一职,负责主持校务工作(当时尚无校长)。或许正是由于我在地委讲师团担任政治理论教员数年,并为地直机关干部讲授哲学课程的经历,使我得以被调至该校,担任教研室副主任,并负责主持日常工作(当时教研室亦无主任)。
这所新成立的干校设施简陋,以至于校舍也只得向已停办的地区银行学校和邻近的百货站临时借用。两者之间相隔一座名为“归马岭”的小山丘,我们教员每日都得攀爬此山,以抵达工作地点,无论是严寒还是酷暑,都倍感艰辛。然而,更令人苦不堪言的是,当时正值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亦即民间所谓的“过苦日子”。粮油实行定量供应,需凭票证购买,我们常常食不果腹,生活中的困苦远胜于工作中的劳顿。
本来我们干校在郊区开荒种了杂粮,每年可收红薯数万斤、麦子几千斤,只要从中拿出很少一部分来分给10多个教职员工,那就完全可以解决饥饿问题。有位年轻同事便提出一个建议:“从我们辛勤劳作的成果中,提取一小部分,每人分得红薯一两百斤、麦子二三十斤,用以缓解饥荒。按照国家规定价格支付,且无需额外提供粮票。”
王校长并未接受这一提议。他强调:“身为教育工作者,我们应当以身作则。我们要求学员廉洁自律,不搞特权,但自身却未做到这一点,这如何能够自圆其说呢?再者,当前全国上下正共度时艰,就连毛主席和中央领导都在过着简朴的生活。既然大家都能做到,我们又怎能例外,非得追求特殊待遇呢?”最终,他们将所收获的红薯和麦子全部上交,毫无保留地交给了国家(地区粮食局)。
全体干校同仁一致认可王校长的决策。究其原因,不仅在于大家思想境界的高尚,更在于王校长以身作则,展现出坚定的思想品质。以下一例足以证明:
某日,王校长的子女与同龄人发生争执,场面一度陷入混乱,旁人难以将其分开。听闻此事后,王校长迅速赶至现场,只对着自己的子女淡淡一句:“不得打架,你不听话,看我怎么不让你吃饱饭。”此语一出,那孩子即刻收起了争斗之心。那时的孩童,与今日的孩子习性迥异,饥饿成了他们最深的恐惧。
此案例反映出王校长及其家庭成员同样面临着艰难的生活挑战。天下父母心皆苦,谁都不忍心看自己的孩子饿着肚子成长。王校长亦然,然而,作为一校之长,他肩负着树立典范的责任,必须与众人同甘共苦。他的这种崇高思想和作风无形中成为了一种“无声的号召”,众人皆以他为榜样,遵循他的决策行事。
为巩固教职工的心理状态,我向王校长提议,于全校范围内举办“苦中思长征,砥砺意志前行”主题讨论,研读毛泽东《红军不怕远征难》的诗篇,并讲述红军长征二万五千里征途的英勇事迹。通过这些学习和交流,让全体教职工深刻理解,我们目前所经历的艰辛与红军长征中的困苦相比,微不足道。面对革命先辈们所经历的种种艰难险阻,我们作为后辈,难道连这点挑战都难以承受吗?我们理应传承革命先辈的坚韧精神和优良作风。此次活动极大提升了大家克服工作和生活中困难的勇气,未对教学工作造成任何影响,大家齐心协力,圆满完成了上级赋予的教学任务。我也因表现突出,荣获“红勤巧俭四好干部”和“六好干部”称号。
我们这所办学颇具成效的干校,却在1962年的机构精简浪潮中不幸被裁撤,教职员工也因此各散东西。我起初被分配至地区人民银行担任科长一职,随后又被调至前郴州市(今北湖区)市委办担任秘书,并在市计委担任副主任(负责主持工作)。市计委主任一职由市委副书记兼市长罗道根同志兼任,他同样是一位思想作风端正的同志。1965年,随着经济形势的逐渐好转,地区财贸干校得以恢复,王宗柏同志再次被调来主持校务。他设法将我调入该校,担任教学科长一职。当时正值“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的运动热潮。由于我们干校在学解放军的思想作风方面表现突出,荣幸地被选为全国财贸系统先进单位的代表,参加全国先进典型会议。王校长认为我的文笔颇佳,便将撰写干校先进典型材料的重任交予我。我倾尽全力,几经修改,终获地委财贸部的审查通过。正当材料准备打印上报之际,“文革”运动席卷而来,王校长也受到了冲击,因此上报先进典型材料的计划就此搁浅。
我当时的困惑不解,怎么连王校长这样思想端正、作风优良的领导,也会被错误地归类为“走资派”,遭受批斗之苦呢?
由于我的思绪混乱如浆糊,因此我既未申请加入反抗组织,亦未随同那些造反者一同竭力抨击所谓的“当权派”。
在运动期间,我亦曾撰写针对“当权派”的大字报,对他们的过失和不足进行揭露和批评。然而,我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绝不夸大其词,更不无中生有。造反派因此视我为领导的“红人”,以为我应当掌握诸多“内幕”。但明知而不言,在他们看来,便是有意为之的庇护。他们甚至将我这个未曾加入造反组织,也未投身保皇阵营的“逍遥派”成员,误解为“保皇派”,甚至对我冠以“钢杆老保”的恶名。
若他们仅仅是口头说说,我或许还能忍受。然而,他们却在财贸战线的造反派报纸上公开点名对我进行讽刺和挖苦。我觉得这分明是试图败坏我的名誉。作为一个注重脸面的人,我自然感到愤怒。
岂知你们能创办报纸,我便以为无此能耐?于是,我这个“逍遥派”也放下了逍遥,独自一人投身于创办一张迷你报纸。我亲自编写内容、雕刻印版、手工印刷,甚至亲自走上街头免费派发。未曾想,这张手写的油印小报竟赢得了众多读者的青睐。
在这份报纸的内容中,有超过九成系取材自“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与《红旗》杂志。唯独《小花园》这一副刊,方是我独立创作的篇章。每期副刊都会刊登一则寓意深刻的小寓言,用以批判那些无论敌友、肆意争斗的现象,以及“打砸抢抄”、“形左实右”、“唯我独革”等不良风气。
尽管这些寓言旨在针对事件而非个人,并未明确指出是何人何事,然而我校的造反派在阅读后,却自行将其中内容“对号入座”,认为是针对他们的讽刺。因此,他们收集了我所发表的小寓言以及一篇《编者的话》,汇编成“批判材料”予以印刷,并将其张贴在干校会议室的墙上,并向全体教职员工每人分发了一份。随后,他们召开了大会议论对我进行批判和斗争。
我想起自己第二次来到干校之前,在前郴州市计委当主任,工作干得好好的,领导对我很器重,只因王校长费了很大的劲把我调过来,我怀着一腔热情,想下决心尽全力在干校好好干一场,把教学工作搞好,用实际行动来报王校长的“知遇之恩”。谁知如今竟落得个被大会批斗的下场,实在是没有料到,也想不通。在这种情况下,我这个不会写诗的人,也不知怎么的,一首打油诗也在脑海里萌生,并即席在批斗大会上吟出:
一片丹心向党红,
愿为教学尽鞠躬。
谁知落得今日况,
动机效果两不同。
任凭烟雾乱舞风,
丹心一颗永远红。
誓将一切献给党,
捍卫领袖毛泽东!
因其“冥顽不灵”,那些掌握权力的造反派遂将我贬至单位食堂,承担起扫地、擦拭桌椅、清洗菜肴、洗涤餐具、烹饪、和面制作馒头等杂役。最终,他们责令我自备背包,徒步约六十里至桥口(地名)。在那里,我经历了为期一段时间的“军事化训练”,训练结束后,便正式宣布我被下放到农村,成为一名“农民”。
我的妻子对我关怀备至,忧虑我独自前往可能感到孤寂难耐,难以承受压力,因此她毅然决然地提出了下放的申请。于是,我和妻子一同于1968年抵达资兴的农村,开始了“农民”的生活。经过半年的时光,我们最终被抽调至县直机关,协助工作。
我始终铭记入党之初,支书对我的一番教诲:“恭喜你正式成为党组织的一员。然而,你需深知,思想上的入党更为关键。这意味着你需时刻牢记自己身为先锋队的一员,无论身处何时何地,何种境遇,都应经得起考验,发挥先锋模范的引领作用……”。因此,尽管当时对于下放的决定心中有所不悦,认为这样的安排不应是我——一个自幼在农村长大、历经各种体力劳动、工作表现优异、多次荣获先进称号的人。幸运的是,通过重新与农民“三同”生活,并深入学习“毛著”,我得到了深刻的教育,提升了自身的认识,领悟到了干部深入基层与群众紧密联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于是,我开始觉得自己被下放并非冤枉,而是一次宝贵的锻炼和学习的机会。
一旦思想豁然开朗,行动便愈发主动。我和妻子齐心协力,全身心投入于劳动与工作中。在经历约三年的农村下放与协助县里工作后,作为一名下放干部,我荣获了“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五好干部”的称号,奖状上赫然盖有地革委和县革委的两枚大印(关于下放期间的感悟,我已撰写过两篇文章进行叙述)。
1971年,我和妻子一同被调回至本地区。她被分配至地区粮食局工作,而我则被派往五七干校。五七干校以学习与劳动为主要任务,相较于机关里坐办公室,劳动强度显然更大。然而,在投身学习与劳动之余,我亦不时挥毫泼墨,撰写稿件投寄至各报刊。因此,我的作品也时常以“豆腐块”的形式,在《湖南日报》、《新湘评论》等报刊上与读者见面。
1972年我看到《湖南日报》上发表的一篇题为《一碗姜汤见深情》的小故事,文章写得简短,只500来字。但我发现其中可有可无的字句还是有一些的,就把它改了一下。在没改动原有结构的前提下,删去了111个字,另外添加了17个字,增减相抵,节省了篇幅约五分之一。当时《湖南日报通讯》正在开展“如何把文章写得短而精”的讨论,我就把修改的稿子,以《极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试改〈一碗姜汤见深情〉》为题投去参加讨论。小文很快就刊登了,编辑老师还写了几句“编者的话”:“欧植竹同志以报上的文章为例,探讨如何使文章更加精炼,这种精神值得赞扬。改进文风是批判修正风的重要任务,让我们共同努力,将这项工作做好。”
实属幸事,恰逢地委办公室亟需一位擅长文字工作的人才。领导们审阅了我的这篇文章后,又发现我频繁在各类报刊上发表作品,便断定:“欧植竹竟能将湖南日报上的文章修改得如此之佳,编辑还特意表扬,并号召大家向他学习,这表明他非常适合调入我们办公室。”我这个社交能力欠佳的笨拙之人,既未提交申请,也未四处奔波求人,更无送礼之举,却意外地从五七干校顺利调入地区首脑机关。
在肩负地委办繁重工作的同时,偶尔也能享受到片刻的宁静。在这段闲暇时光里,我秉持着对本职工作的敬业精神,继续投身于报刊投稿,并尝试涉足文学创作领域。自1973年《湘江文艺》第二期刊登了我的《巧妙地安排细节描写——读〈飞跃〉的杂感》一文后,我的文学作品便在多家报刊上接连问世。我的文艺评论竟意外地赢得了省文联诸多师长和领导的认可与赞誉。在省作协第三次代表大会及省文学评论工作大会上,我均受到了表彰,并被纳入我省“近年来崭露头角、思想敏锐的一批理论新秀”之列。我的寓言作品在《湖南群众文艺》上发表后,更是在庆祝建国三十周年的文学竞赛中荣获佳绩。1978年,省作协吸纳我为会员;1979年,随着地区文联的恢复,我有幸担任专职副主席一职,主持日常工作(文联主席由地委宣传部一位领导兼任)。在省第四、五次文代会上,我还被选为省文联委员、省文艺理论研究会理事、省儿童文学创作委员会委员。此后,地委更将我的职务转为正式编制,使我得以担任地区文联主席。组织上还曾调我至地委组织部任职。这一切充分证明,“文革”并未对我的职业生涯造成任何负面影响,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当时办事(包括干部选拔任用)的公平与公正。
这就是我在“文革”期间的经历。我这个基层干部,犹如一只“井底蛙”,视野狭窄,目光短浅,所以当时对“文革”的认识是片面、肤浅甚至是错误的。那时流行一种说法,毛主席发动“文革”是他晚年“犯了严重错误”。我这“井底蛙”也就以为,毛主席这位伟人,可能是他毕竟年老了,再没有过去那么英明,看到苏联出了个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也就以为“中国赫鲁晓夫就睡在我们身旁”,因而发动广大群众与他们进行斗争。而我这个基层干部所看到的,只是身边的一些思想作风蛮好的领导也被当成“走资派”来整,就觉得毛主席发动“文革”真的是“晚年犯了错误”。
从当前形势来看,毛主席当年的判断无疑是正确的。
我这个曾经的“井底之蛙”如今终于得以窥见毛主席当年的一些演讲,宛如“拨云见日”,使我从迷惘中豁然开朗。
毛主席曾言,马克思与恩格斯未曾预见,他们的继承者伯恩斯坦与考茨基竟沦为反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所创立并领导之党派,如德国社会民主党和法国社会党等,在两位伟人离世后,竟转变为资产阶级的政党。
毛主席认为:中国会不会放弃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关键不在城乡基层,而是在上层,尤其是中央。如果在中国自上而下出修正主义,它的危险比自下而上出修正主义要大得多,也快得多。他说:“先从豺狼入手,再对付狐狸,这才是抓住了问题的关键。若不从当权派开始,则难以解决问题。”
毛主席曾言:“我屡次提出核心议题,却屡遭误解与抵触,阻力重重。即便我的言辞被置若罔闻,也并非仅关乎我个人。这关乎国家的未来,关乎党的未来,关乎我们是否会改变初衷,是否会继续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行。......若照他们的做法行事,那么我和无数先烈们倾注一生的努力将化为乌有。”
“无私之心,我常怀忧虑于我国百姓所承受的困苦与艰辛。他们渴望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因此,我始终紧密依靠群众,绝不允许他们重蹈覆辙。”
“在新中国成立的历程中,牺牲了多少生命?这一问题有人深思过吗?我个人倒是认真思考过。”
“我即将与马克思相会,如何向他们交代呢?你只需留下我的一点修正主义遗风,我绝不从命!”“那些支持我们的人,转瞬间便能化身为修正主义者。”
……
读了这些语录也就明白了,毛主席就是为了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避免苏联红旗落地、亡党亡国的悲剧在中国重演;是为了捍卫和坚持马列主义,防止修正主义篡党夺权;是为了我们的社会主义道路能继续走下去,不让资本主义复辟;是为了全国老百姓不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不让革命先烈的血白流了。毛主席是一如既往英明、伟大、正确,是特别有远见,有预见性的。
我们渐渐意识到,党内确实潜藏着一些热衷于资本主义复辟的“爱资病患者”。他们渴望回归到剥削和压迫他人的生活方式。其中一部分人,其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本就扭曲,投身革命、加入党组织只是为了谋求官位,而官位的追求不过是财富的另一种形式。这类投机者一旦跻身各级领导岗位,便沦为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不遗余力地为资本家谋利,从而催生出一批百亿、千亿富翁。他们本人也从这种“有偿服务”中获益。还有一些人,原本品行端正,思想作风优良,却在金钱的诱惑和“糖衣炮弹”的攻击下变质,堕落为腐败分子,有的贪腐金额高达数亿。用老百姓的话来说,这些人是“好蛋变坏了”。
由此可见,不仅那些原本思想纯净度不足的人们亟需学习和思想改造,即便是优秀的党员与干部,也需持续学习与自我革新,以防滑向堕落。这充分证明了毛主席运用文斗手段,成功改造人们的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其转化为无产阶级思想,从而挽救了党内走资派,并使他们与人民群众一道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何其英明、正确的举措啊!其动机是如此崇高,其眼光是如此锐利,预见性是如此卓越!
当然,我承认“文革”期间确实存在一些失误与问题,例如过度扩大打击范围,将一些优秀的领导者误判为“走资派”进行批判,以及个别人违反政策采取了一些极端措施。然而,对于这些错误与问题的成因,我们必须进行深入的剖析与思考。
除了“文革”作为前所未有的群众运动,由于缺乏经验导致不可避免的一些失误之外,其发生还另有深层次原因。这其中包括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故意误导,将斗争方向引向群众之间的对立,以及实施“形左实右”的策略,违背政策宗旨,破坏了运动的初衷。比如,他们无视毛主席“以文斗代替武斗”的明确指示,强行推行“武斗”和“打砸抢抄”,导致了严重的后果。这种恶劣行为,怎能将责任归咎于毛主席?将“文革”期间出现的错误和问题全部归咎于毛主席,这是极不公正的!毛主席发起的这场运动,本名为“文化大革命”。毛主席一贯反对武斗,他认为武斗只能触及身体,而不能触及思想,唯有文斗才能有效改造思想,实现“文革”的目标。这一点,所有亲历“文革”的人都有共识。
这便是我对“文革”时期所持的情感与见解。身为当年的“井底之蛙”,我对于那时所持有的片面与错误认知深感羞愧,同时,也为如今自身的成长与觉悟所取得的进步而感到由衷的欣慰。